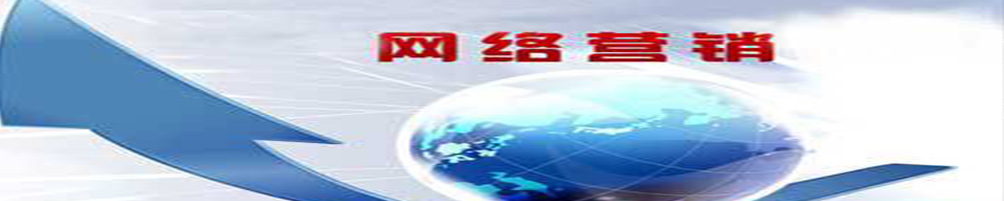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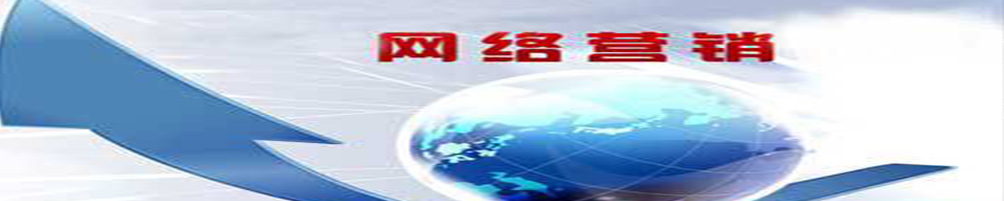
年第6期总第期
主管:中国西部散文学会
主办: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山东分会
社址:山东济南国际旅游度假区
杂志:《黄河文艺》(纸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刊号:CN63-/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翻越父亲那座山......
安雷生
无论您漂泊到何处
我都会把您记在心里
题记:人生的父是我们每个人要跨越的山,天上的父是我们每个人必敬拜的主。一个孝顺勇敢的孩子,定当若父地扎实修为,砥砺前行,做最好的模样,衍献出至善的光景来,不负亲族、故里和社会的养育与期望。
1“啪”!父亲表情恼怒地迟疑了只一霎,最终,扬起的巴掌,还是打在了我的脸上。
印象中,那是父亲头一次揍我。
“孩子,咱撇家舍业,是来干什么的?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是还有那么多同学对你好吗?螃蟹过河看大流,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9年前那个不一般的春天,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备战高考,一向认真用功的我本该埋头学习,却因为一件琐事打扰得情绪低落,甚至产生了转学、弃学的念头。
若不是父亲的赶巧了到来,后果将会非常糟糕,追悔莫及。
那时,我就读的博兴县教育局英语班,专门开了个文科小组,我们六个人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学习。因为年前所有功课早已结束,剩下的时间便是随着老师的辅导进行强化训练,以做模拟试卷和自我复习为主。
有一次,班主任王洪兴叫我发放语文历史试卷,大班里有个男同学是县城单位的通校生,成绩一般,那天他迟到了,我就把卷子放在了他座位前课桌上。不知怎的几张卷子找不到了,他就到文科小组找我要,说我没给他,嗷嗷着耍态度,还抢走了我的,和我产生了推搡动作。而班主任王老师看他人高马大,又是县商业局机关子弟,不问青红皂白,便偏向于他,当着同学们们的面无缘无辜地训斥了我。
我想到平日里为班务够积极勤快的,晚上还没少骑着自行车护送王老师的家属,大家尊称她师母,穿过东关老城里黑咕隆咚的胡同大街,医院上班。更有父亲曾经捎来才兴的过滤嘴香烟,让我送给王老师抽,虽然我不愿意做这事,可放在抽屉里也占空子,尤其是不能枉费了爹为我学习“打点”的良苦用心,便硬着头皮去了他家。王老师只是口头上讲我父亲任一个五千多人口的大队党支书有多棒等等,实际上辜负了他个别照顾好我学习的托付,临近高考几个月了,学习那么紧张了,他居然让我和他印习题,浪费了我一个早晨的宝贵冲刺时光。这回我为同学们付出了那么多,不表扬也就算了,怎么不主持公道,乱捏瞎扯?就气不打一处来,感觉学习环境太差了,头嗡嗡发胀,便打算转学到一中文科班,不成便直接弃学回家,闷闷不乐中复习自然也没有了劲头。
过了没几天,正好我爹带领村办厂门负责人来县城办事,顺便看我一下。他为文科小组的同学们带来了村里园里的苹果。我就当着大家面发了几句牢骚,又嚷嚷不在这里了,非转学不可。他愣了半天,眉头紧锁,不容我继续往下说,即百般怜惜地安抚我一定好好学习,再有三四月就高考了,换了地方一时熟悉不过来,又要对接课程,会生出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来,必然影响到学习。接着,他又把我喊到外面屋山槐树底下,苦口婆心地劝了十五六分钟,不知怎么的,可能是我身处快节奏学习状态一时还走不出来,仍然固执己见,并且发狠要弃学到淄博去跟着二叔干建筑,也不受这窝囊气。
情急之下,他便掴了我。
难耐的沉默里,父亲手有点哆嗦地掏索出了一包烟来,划了几次火柴才点上。我知道他一向不抽的,掖着也是为了敬人,便止住了哭泣,捂着脸低下了头去……呆了一会,我思来想去到底父亲说的很有道理,确实这件事简直就是鸡毛蒜皮,自己哪能钻牛角?更不该因此让它干扰了复习高考的大事。而我仿佛又看到了他既要在村里忙忙活活,又要在责任田里干重活;母亲上崖了还得烧火做饭,晚上拧蒲草手工编织样品一直熬至过半夜……
爹,一耳光将我打醒了!
至此,我便愈加横下一条心,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让老师同学们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也为了不辜负一家人的希望,开始重回先前的状态,继续发愤学习,做最后的冲刺。
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个月后,我如愿以赏地考上了大学。可是,提起那段经历,仍不免有些后怕,一如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每每回忆往事,我禁不住思潮翻滚,感慨万端,可以说没有爹那一巴掌怎有我赶考圆梦走出黄土地的机会?就更别指望得以坐在办公桌前勤奋笔耕,不断进取,很好地与文学结缘,搞出什么明堂了……
一阵清风吹来,远望青黛隐约,雾岚缭绕的群峰峥嵘,爹慈祥的音容笑貌复又浮动于眼前……
年6月20日凌晨1点16,一声霹雳猛地从我们头顶炸响,爹在博兴县湾头村老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猝然离开了我们。
深夜,我关了手机充电,忽听妻子敲我卧室门,说,我姊妹打来父不知怎的变得糊糊涂涂的了……医院的急救车去。我知道那是她怕我着急的托词,遂立马穿衣准备回老家,可汽车昨晚停在了湖滨大酒店,电动车恐怕电量不足,想骑自行车又怕来不及,懂事的妻子就叫起了女儿来,说和我一块回去。一会儿,姊妹又来电话说正在抢救,我变了调地回话一定要尽全力。
车子驶出小区,我光催女儿快开,她埋怨我自己近视眼跑太急了看不清路。走到湾头老槐树西时,我眼里已经噙了泪水,便知道乃亲人感应,恐怕凶多吉少。又南拐不到百米,往西折,黑乎隆冬的,没见到救护车,我感觉情况极可能一败涂地了。等我进到院子、屋里,堂哥也在,我娘在炕上托着爹的下颌,以免他张着嘴。急躁躁的我爬到炕上,悲痛欲绝地喊着爹哦,爹哦,爹哦……你咋走得这么疾,没让我看最后一面,也没说下什么……眼前发黑,痛啜流涕。大哥不让起声,说去叫人买寿衣的了,先穿好,入殓再哭。爹体温还暖和,就是嘴唇发开了凉,模样还是那么平静安详。
我真的不相信,爹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老人家一向身体强壮有力,平常很少生病,就是出殡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开始打理怀念他的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曾觉得爹已然不在了。
早就想着回趟老家,就是瞎忙,分不开身。我是多么的懊恼啊!平常耽于文学创作,惜时如金,就是回去一趟,也都匆匆忙忙。平常我回家都是放下东西、钱,匆匆忙忙和他说几句话,便意犹未尽却腚底下窜火般地撂下句话,“再来着说吧”,千言万语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信誓旦旦,而每当回家却又以却也真是文字营生缠身为借口,一回又一回地把前面大嘴獠牙许愿的亲情唠嗑、交结、相处、厮守,以心不在焉、偷工减料的短暂应付潦草待持,这样白话时,也感觉就起身走了。而每次他都送到我屋后头大胡同边,看着我开车才回家,当时也没有看出他老了多少。可岁月无情啊,那天我突然感觉爹八十的多的人了,我还没有专门拿出工夫扎扎实实和他好好处处呢。
总感觉发愧地撂下那句话,而等下一次来了,却还是如此炮制,循环往复着。
好在我当海警的二小子每次从厦门探家回来,我都要先领他去湾头看望爷爷奶奶。而和孙子拉起来,爹高兴地这问那,像是十几年没见过面似的,那个执拗、热乎劲啊,就甭提了。老人们都说隔辈人格外亲,真是这样的。
过去,我在离家仅十五六里的县城住所,面南写作,感觉踏实,外出也牵挂得无恙、“趁手”,可现在,泪眼婆娑的自己心中已经空得恓惶、生疼,像刚刚挣断线的风筝,一下子被撂慌得跌跌撞撞,头晕目眩,时空错乱,一派失魂落魄,不能自拔……
我爹是个孤儿,生于年3月15日,这是身份证上登记的年纪,实际上有出入,因为他才六虚岁时,我奶奶就病故,十虚岁上,我爷爷又撒手人寰。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农村老百姓日子困苦不堪,我爹年纪很小,自己双亲相继作古,自己难以记着。关于他的生日只能问我五服以里的大嫂,回答是大概在你二大娘过门后几天,到底具体在哪一天?没有谁记得住,至今也稀里糊涂着。
爷爷去世时,我大爷娶亲一年多,兄弟俩,再加上我大娘,三个人相依为命,熬着饥寒交迫的时光。我的老姑出嫁在锦秋湖东南乡的祝家营,为了接济爹,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常年给爹做着单寒衣服、鞋帽。我们一大家七八个兄弟才给爹过了今年的生日,后来不久,我就想着买上新上市的西瓜在回趟老家看看。其间,倒下快一年的小姨病危,我便给爹打了电话让他在老槐树以西道北面等着,我开车接他去孟桥探望。我们在小姨病床前站了二十多分钟,唏嘘心疼她所受的活罪。然而,谁成想小姨故去十七天后,我还没耽个空,还了回家走的心愿,爹竟然撒手离我们而去。
爹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文友陪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到湖滨大酒店吃饭,我也曾冒出接爹一块来坐的想法的,却考虑再三还是作罢,谁知这居然铸成了我终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仅仅过了三四个小时,爹就跟我们永别了。那个酒店我已经若干年没去过了,一沾酒车也没法开了,便放在了那里。我不知道这里面隐藏着何种玄机,为什么我那么旁若无事地坐在离家二里多的县内体面接待场所里谈笑风生,觥筹交错,却浑然不觉死神已然行进在了掠走爹的路上?
事后,我就反复寻思着倘若是自己有半点感应的话,我也会断然放下一切活动,双膝长跪不起,祈求阎王爷无论如何千万手下留情,允许我把爹从鬼门关里拉回来。
爹,你老人家就那么冷淡、漠视和讨厌着我这个儿子吗?今年春节,以及平常你得到的玄然呈示和梦境,还有那些朦胧的预感之中,难道就没有察觉隐含着什么逆端背卦?难道你没有从中揣悟得出什么欠妙之处哦?还是你接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却害怕吓着我们,一直不便于给晚辈们讲出来?或许,你要是能打个点给我的话,那样,儿子也不至于深陷遭受噩耗突然袭击,堕入补偿之举没处可施的自责、怨恨渊薮了呀!
生命的最后一刻来势汹汹,爹呀,爹,您,您,您怎么没有留下一句话?更没有等到让我赶来家,瞧上哪怕仅仅一眼,便匆匆上路了?
长歌当哭,只会带来更加剧烈的心如刀绞。而那样的悲痛的情景我一生岂能忘了?
“那天上午,我双膝跪倒在爹安息的屋门前。香火缭绕哦,悲哭涟涟。主事扬起菜刀,拍碎了一个倒扣的黑碗。一直忧怯的开丧高呼,还是降临在了老家小院。蓦然我觑见老槐树下爹依偎进了爷爷奶奶怀里。凄喜交加,亲人断肠作别,又隆重相见。那天上午,我们围着爹的新房正转三圈反转三圈,洒下五谷、棉花种子,为爹送行、超度,情意缱绻,祈求他一路通达极乐西天。我磕狠头静立在荆草间,不为赏景,只一遍遍耽味爹的一世人格如灿。我们焚烧那么些族人们敬献的信物,不为排场,只为爹在那边什么也不缺,献上人间最后的温暖。那天上午,我抬起头向着天上的白云看了又看,不为守候什么,只为乞福、祝愿于心间垒起玛尼堆,发誓勉力修为,筚路蓝缕创业,明智,弘德,孜孜向善。听天边梵唱如缕,参悟轮回想爹化羽成仙,俯瞰尘世。保佑我一家旺祥、平安……”
送葬回来,情绪稍事平静了一会,我便理性的思考着:是我心地不好使吗?是我迷瞪过了火?是我不负责?是我没有过早的注意到爹耄耋之年可能冒出的不测病情?是我……我双手抱头,两耳嗡嗡作响,感觉天旋地转,内疚隆隆,幻思翩联,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上了年纪的街坊们说,很多类似的人都是这样无征兆地猛不丁发作,旁边人眼看着他倒下去,也帮不上忙,不等医生赶来,几分钟便不行了。但是,在感谢人家好意劝解我不要过分自责之余,我却不能轻易因之宽心,更不会顺着这个跐脚溜下来,苶了瓜葛了事,抽身旁顾,不作牵扯、检讨了的。
关键时刻,我不光没有守在爹身旁,而且,还是处在两个相反的气场,在爹即将跌进万劫不复的火坑之时,我没有先于他浑身如触凌迟之讯,没有在他老人家一片担惊受怕中抱住不幸的爹,没有由衷地体恤着爹,安抚着爹,呵护着爹,好让爹不失鼎持、慰藉地承受剜心的痛苦,平心静气,魂魄福乐溶溶地作别人世。现在,我一个人什么样的忏悔甚至自虐,都无法挽留住他老人家的生命了,我是个不孝之子啊!
我闭门反思,深味着这样的时空注目下凌厉遭遇的发生,完全与别的因素无关,应该是我素常的修行出了问题,指认无疑地袒露了自己的持应、兑报短板。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过不去——如果我道业确凿充实渐丰,恩囤、炼担到了,怎么可能会这样父子相间,彼此“舍弃”?
看到我那样凄凉难受,有几个亲戚朋友替我宽解说:你爹也是为你好哇,是为你们兄弟姐妹们着想,相信你自己也绝对不会料到你爹就这么去了而袖手不管的。你能这样完揽其疚,责备自己,折腾自己,说明你心肠不坏,而你爹更是做了一辈子的好人,临期末晚也没赚讨人嫌,这是祯泰之象呀!
可我强按住哽咽,执拗以对:哪里哦?一点也不是!
一个晚辈,在爹弥留之际,都没有赶上,没有在跟前紧紧握着爹的手,双眼盯着爹所受的煎熬,没有看着医护人员紧急抢救他老人家,没有和蔼地跟爹说最后几句可心的话,根本算不上尽到了人子的本分,这个人哪里算得上是好东西?更不是什么好心碰到了自己左右不了的孬事了!
想想看,当饱经风霜雪雨受尽坎坷磨难,含辛茹苦的父亲在临终的一瞬都没有被围在儿子撕肝裂肺的恋恋不舍中闭眼,这个儿子没赶上现场为他做些人工呼吸什么的,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开脱?又有何脸面人前人后的嘚瑟?
扪心自问自己哪里是个好儿子呢?作为拳拳人子,我怎能不久久愧馁、怅惘,翻江倒海?
我,就是那个注定一辈子都因此而良心不安的儿子啊!
2连自己生日都不能认定在哪一天的爹,到离世都不知道其外祖亲具体在哪个镇村。
我奶奶年出生,姓陈,小名兰香,祖籍江苏省沛县小陈家村,这是口语,前年我从沛县的地名录里查了一下那里与陈家有关的至少五个庄。
大前年,我和爹到不远的南河东村去拜访我五服内九十岁的老姐姐安丽生,问到了一些我奶奶的情况:身个高,白皙,会纺棉花。家乡大涝,光景潦倒,奶奶上坡剜菜时,让挨千刀的人贩子哄骗出去,流落山东。
后被齐鲁大学毕业,就职于省政府,在山东医院的我二爷爷经济南顺小清河而下,领来老家。
那时奶奶才十五岁,加之兵荒马乱,贫穷落后,日子恓惶,除此之外便再没了其他信息。后来,奶奶跟我爷爷成亲,由于贫穷落后,和家乡也没有书信联系,更没有再回去过。年11月18日,奶奶因痨病去世。年春节期间,我表示要替爹回去寻外祖亲,基本不抱任何希望的爹两眼忽闪了几下,长时间地看着我,像是从迢遥的苍茫纵深走来了一个几十年不见的旧友,矍铄的他昏花的两眼慢慢觉醒,开始发出知己相遇,点燎一壶陈年老酒荡起的明亮幽光。
由于被骤然降临的祥讯击中发懵发痴发晕发笑,一时不知所措,他的嘴久久微张着,笑容挂长了,肉劲不足以支持住快乐的神经,想松弛下来又不甘不肯不便,以至于疲劳难当,放下又掬起,那是我从没见过的由沉睡的史册中复兴辉煌神态。是因着意外的喜悦、福祉的撞坏和亢奋点的抠门而合成的迥殊欢乐与感激,是从爹的内心油然迸发的,毫无做作的真挚流露,是幸福降临之下惊悸倏忽、虔敬漫漶、开慰忐忑,掩饰不住的,所以,才如此明亮和耀眼。还有,爹兴奋里带了一丝我莫不是心血来潮的将信将疑,待重新笑出来时,自我安慰又旌表我似的忐忑着说了声:好啊!
过去,爹孤苦伶仃受穷,挣扎于生计困境,参军奋斗,回村当不脱产的干部,忙忙碌碌了一辈子,寻亲条件差,去了几趟沛县,打探来去,也没有找到。现在一切都好了,爹又上了年纪,不能出远门了。
所以,当我主动提着手替爹完成总是困扰着他的身世问题时,爹老脸绽笑,久违的光泽伴着汪着的泪花从他心头爆出。爹的殷殷情结一定跟奶奶的来路一道,奔走在了那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寻亲的路上了。
到了7月份,我把这些信息到发到沛县网上后,得到了当地爱心文友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回老家把这些情况说给爹时,他高兴得不得了,毕竟这是他一辈子的夙愿,更是奶奶在世时都一直耿耿于怀的未了情。
然而,我整天东奔西颠,没有及时兑现对爹的诺言。年,我主持的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山东省分会搞的文学活动多,牵扯了我的主要精力;年初,我想去沛县寻亲了,又遇上新冠风声太紧,承诺才见展开,缺憾破门而至,就在这年农历闰四月的二十九日凌晨,爹却猛然伏于无常。
行进在马路上,或者到集市、人多的地方,看见衣着、个头和凉帽和他相近的人,总疑心地瞅几眼,以为可能是爹出门遇到了。
空荡荡的小区院子长道于我看来,正是希望和奇迹最会扶乩着我的心性收成爆出的质地,我甚至几次绰绰约约感觉爹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若有所务地从远处驰来。
一阵风儿吹来,眼前的影像被硬生生掠去了,不情愿地消失了,而无法遏制和枯竭的是我黯然神伤的泪水,我不知道明天升起的太阳能否烤干那扑簌簌的汛势……今辈子我就这样猝然惊涛拍岸,决绝断崖,再也见不到了爹。
杜鹃啼血,我山呼海啸的串串嘶哑呼号注定沦入宇宙黑洞,从此便没了声息?
一位七大娘没念过书,却曾经讲过这样一句俏皮“名言”:亲戚们哭爹,破声啦气;媳妇子哭爹,虚嫌冷气;干儿哭爹,驴驹子放屁;亲儿哭爹,惊天动地。我无意贬低谁抬高自己,只是引用而已,其实这里面跟实际情况肯定有些出入,但我却是情愿再不如人,即使被打倒在地,踩在脚下,也不愿意爹走了的呀!
一些清平、美晏、祥和的时光里,一些很好的地方,比如一块艳阳下的花荫凉,一缕缕爽朗的风里,一道景色绝佳的山地、河塘,一处高雅标致的楼馆……总想着和爹一起享受,也朦朦胧胧看见了爹飘忽其间的音容笑貌。
在他去世一个月时,我应邀到济南去出席中国国际文化促进会的一个书画大展和香山论坛,面对那么出类拔萃的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面对那么些来自全国各地协会领导、书画家、文化大咖,我不断地埋头工作,斜看花树,读书览卷,偷偷抹着不断流出的眼泪。
七八年前,我和姊妹商量请他老人家到长岛、江南转转玩玩,姊妹说人老了广解手都很不方便,也加上自己工作忙,一直没有陪爹出去旅游。
还在去年春天,我开车和他到不远的本县西闸村麻大湖北岸去逛,事先买了菜、酒,大半上午就那样在熙熙攘攘、声乐嘈杂中过去了。走出湖区的路不长,我提着暖壶和茶杯酒具径直穿过一片绿化带,而回头看时,父亲却慢慢落在了后面,我一下子唏嘘着,“人老了还是这个样啊!”我真的愧悔交加,就在我日复一日应付职场潜心写作,巴结大人孩子小日子的时候,爹竟然变得老态龙钟的了,军人出身的他一向刚强健壮,在我们兄弟姊妹从不显出软弱。
父子连心,血浓于水,一点都不错。父亲去世以后,每每想起他,无论心里怎样使劲劝解自己,往往还是禁不住伤心落泪。这种痛苦尤其在淫雨滂沱的时候更加强烈,阴阳暌隔,我们坐在楼宇里或闲适地读书、喝茶、看